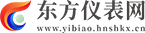傅雷藏书发现记 | 陈占彪
周末刷手机,突然看到新闻:2023年5月19日,傅敏先生与世长辞。就在一年零三个月前,2022年2月19日,笔者曾受邀前往傅敏先生家中拜访过他。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傅敏先生在讲述他处理他父亲藏书的经过
拜访他的原因是,笔者曾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意外发现傅雷先生的一些珍贵藏书,于是不免多想,这些藏书怎么会流转出去,并最终到了这里呢?空想无益,傅雷先生的次子傅敏不是在的吗?直接问他一下,或许他会知道的吧。于是,通过出版社的朋友和他取得联系,大概他也为此而感到高兴吧,于是约笔者前往浦东家中一晤。
现在,笔者将自己陆续发现的傅雷的法文藏书,以及傅敏先生对笔者所述他处理他父亲的藏书的情形,一并介绍于此。
一
1961年7月31日,傅雷在给他的好友刘抗的信中说:“愚兄未置一产一业,除大量藏书少许藏画,别无所有,真是惭愧惭愧!”(傅敏主编:《傅雷著译全书》第26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页。)那么,傅雷的书都哪儿去了?
初衷只是找一些莎士比亚剧作的插图——2021年10月26日下午,笔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外文书架中,找到了1907年文艺复兴出版社(The Renaissance Press)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洋洋四十卷,每卷卷首都有一幅精美插图,但可惜每卷也就只有这么一幅。
因为各个国家的文学艺术类书籍都放在一起,看完之后,正要退出,在距离《莎士比亚全集》不远处的书架上,突然两本书映入眼帘,白色的书脊上用毛笔写着“H.TAINE PHILOSOPHIE DE L’ART 1”,“H.TAINE PHILOSOPHIE DE L’ART 2”。
这应当是丹纳的《艺术哲学》吧。再想,傅雷先生不是翻译过这本书吗?于是随手取了下来,打开一看,原来这两本书的白色封皮是后来装订的,真正的封面是淡绿色的,封面后前衬的左上角,有着一个签名,“Fou……Mai 1929”。这名字签得行云流水,可以看出前面三个字母是“Fou”,但后面是什么却并不能辨得,纸张泛黄而发脆,得小心翼翼地翻。
看到这两本书后,再往下看,又看到一本绿皮封面的书(上图)。拿起一看,是一本《艺术史二十讲》(L. Bordes, Vingt le?ons d’histoire de l’art,J. De Gigord,1927),心里又一阵惊喜,因为傅雷也有一本《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闻名于世,这两者书名多少有些相似。打开一看,封面后的前衬右上角仍然有一个“Fou……”的签名,和前一本书一样,特别是左下角明确地写着“傅怒安 一九三○ 六月购于巴黎”几个虬劲有力的汉字。看到这些字,心情十分激动,因为现在可以确凿地说,这些书正是傅雷先生的书。而这“Fou……”也正是傅雷的法文签名,虽然还不能完全辨认。这意外的欣喜几乎让昏黄的图书馆顿时一亮,也让我不得不平缓一下呼吸,以便细细地咀嚼并品味这巨大的喜悦。
随后,我又看到了奥古斯特·罗丹的《艺术论》(Auguste Rodin:L’Art,Entretiens Réunis Par Paul Gsell,Paris:Bernard Grasset,éditeur,1924。上图)这显然是傅雷所翻译的罗丹口述,葛赛尔记录的《罗丹艺术论》的原书。这本书的封三上用法语斜写了一句话,落款也有他的法文签名,并有“1930”字样。
大概还会有的吧——笔者便有意识地一本一本去排摸,果然,又发现了三本《独立绘画》。分别是两册相同的《法国独立绘画I:从莫奈到邦纳德》(La Peinture Indépendante En FranceⅠ: De Monet A Bonnard)和一册《法国独立绘画Ⅱ:从马蒂斯到赛贡扎克》(La Peinture Indépendante En FranceⅡ:De Matisse A Segonzac),作者是Adolphe Basler和Charles Kunstler,出版者为Les Editions G. Crès et Cie,出版年份都是1929年。这套书介绍了各种现代派绘画,后面都附有丰富的插图,内页虽然有看过的痕迹,但总体来说比较洁净。只是在《法国独立绘画Ⅱ:从马蒂斯到赛贡扎克》这册书的封面后的前衬右上角有傅雷的法文签名“Fou……”,左下角竖写着“傅怒安一九三一年五月巴黎”。其他两本第一册都没有签名——其中至少有一本是傅雷的书吧?
傅雷的法文签名行云流水,一时难以完全辨别。晚上回家后,急忙查阅刘志侠的《傅雷的欧洲岁月》(《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1期)一文。刘志侠在文章中将傅雷从1928年到1931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写给他的法国好友达尼埃鲁的一些信及傅雷的一些其他的法文材料,挖掘了出来,做了集中的介绍。这中间附有一些插图,从中可以看出傅雷在信中的签名和他在笔者手上拿着的这些书上的签名完全一致。
可是,傅雷的法文签名具体是什么,却一直没法弄明白。笔者曾向懂法文翻译的朋友请教,对方未能辨识;到傅敏先生府上拜访时向他问询,他亦不知。大概一年多之后,我忽然想到,傅雷早年发表的法文文章中,应当有他的法文署名,何不查看一下?立即翻看刘志侠先生的《傅雷的欧洲岁月》一文,根据该文附图中的《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通报》刊载的,傅雷于1931年5月1日在意大利地理学会和扶轮会演说的消息中他的名字,以及傅雷于1932年1月在法国《知识生活》(La Vie Intellectuelle)发表的演说稿《十字路口的中国》(La Chine au Carrefour)一文的署名,以及1931年9月傅雷在法国的艺术刊物《活艺术》(L’Art Vivant)上所发表的《现代中国艺术的恐慌》(La Crise de l’art chinois moderne)一文的署名,都可以看出他的外文名是“Fou Nou-En”。
另外,在2018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26卷《傅雷著译全书》各卷的一些卷前插图中,也可以看到他的外文名就是“Fou Nou-En”。比如,在1934年3月3日,傅雷致罗曼·罗兰的书信中,1934年6月30日罗曼·罗兰给他的回信中,1936年,傅雷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一书的封面上,1937年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初译本的封面上,都有他的法文签名。
傅雷在这些藏书上所写的让笔者一时难以辨认的签名问题因此迎刃而解。而且它的法文发音和他的中文名字“傅怒安”的发音也大体相合。
二
众所周知,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其实,他对一切艺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绘画、音乐、文学等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他曾说自己“趣味比较广,知识比较杂,但杂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傅敏主编:《傅雷著译全书》第22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336页。)他对音乐极为看重。在他看来,中国的音乐“在没有发展到顶点的时候,已经绝灭了”。在1933年,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时候,他就说:“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根本办法,尤不在政治、外交、军事,而在全部文化。我们目前所最引以为哀痛的是‘心死’,而挽救这垂绝的心魂的是音乐与戏剧!”(傅敏主编:《傅雷著译全书》第23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325,333页。)从中可以看出,他把音乐强调到了非常重要的地步。
傅雷说他曾在1929年到1931年期间,“因为爱好音乐,受到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作品的启示,便译了《贝多芬传》。”(傅敏主编:《傅雷著译全书》第22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338页。)后来傅雷还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作品。可见,他成为一个翻译家,与他对音乐的兴趣颇有一些关系。
2021年11月16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音乐类图书中,笔者看到一本罗曼·罗兰的《古代音乐家》(Musiciens d’Autrefois,Librairie Hachette,奇怪的是这本书查不出出版年份),这已是这本书的第10版了。书的前衬右上角仍是傅雷的法文签名“Founouen”。
傅雷的一些音乐知识当来源于这本书。1935年,他发表的《音乐之史的发展》,将音乐的重要性,特别是远古以来音乐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做一梳理。文章后面他附白,这篇文章的取材“大半根据罗曼·罗兰著的《古代音乐家》‘导言’”。(傅敏主编:《傅雷著译全书》第23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346页。)1955年,他又翻译发表了罗曼·罗兰的《古代音乐家》中的《论莫扎特》一文。可见,这本书对傅雷的重要性。
1961年5月23日,他在给傅聪的信中说到柏辽兹的时候,就提到了罗曼·罗兰的这本《古代音乐家》。他说:
“你既对柏辽兹感到很大兴趣,应当赶快买一本罗曼·罗兰的《今代音乐家》(Romain Rolland:Musiciens d’Aujourd’hui ),读一读论柏辽兹的一篇。(那篇文章写得好极了!)倘英译本还有同一作者的《古代音乐家》(Musiciens d’ Autrefois) 当然也该买。正因为柏辽兹完全表达他自己,不理会也不知道(据说他早期根本不知道巴哈)过去的成规俗套,所以你听来格外清新、亲切、真诚,而且独具一格。”(25-122.)
我还看到一本卡米耶·贝莱格( Camille Bellaique)的《莫扎特》(Mozart,Librairie Renouard,1927)。这本书分莫扎特的生活和创作两部分内容。这本书虽然没有傅雷的签名,但是这本书末尾的内容,当正是1955年3月24日,傅雷为傅聪学习音乐时所翻译的关于莫扎特的材料,傅雷名之为《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这个题目也正是这部分内容的核心观点。1955年3月27日,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说到他译后的感受:
“从我这次给你的译文中我特别体会到,莫扎特的那种温柔妩媚,所以与浪漫派的温柔妩媚不同,就是在于他像天使一样的纯洁,毫无世俗的感伤或是靡靡的sweetness[甜腻]。神明的温柔,当然与凡人的不同,就是达·芬奇与拉斐尔的圣母,那种妩媚的笑容决非尘世间所有的。能够把握到什么叫做脱尽人间烟火的温馨甘美,什么叫做天真无邪的爱娇,没有一点儿拽心,没有一点儿情欲的骚乱,那么我想表达莫扎特可以‘虽不中,不远矣’。”(傅敏主编:《傅雷著译全书》第24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页。)
笔者翻阅这本书时,发现在这部分内容的原文上有着比较多的划痕。应当说这本书正是他使用过的(下图)。
1956年7月18日,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两百周年,傅雷应《文艺报》之约撰写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一文。这篇文章中一些内容和观点正来自《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一文,或者说来自于卡米耶·贝莱格的《莫扎特》一书。
三
2022年3月9日,笔者在图书馆漫无目的地翻书的时候,在文学类书籍中,不经意间又发现了傅雷的几本藏书,都与法国诗歌相关。
一本是《法国新诗选集》(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Fran?aise,KRA 6 Rue Blanche Paris,1928。上图)。这本书收录了包括波德莱尔、纪德、普鲁斯特、瓦莱里在内的六十位诗人的作品,看来比较权威,也比较受欢迎。这本书是当时的最新修订本,已经印到第25版了。其前衬右上角是傅雷的法文签名“Founouen”,左下角竖写着“傅怒安一九二九,十月,于巴黎”(下图)。
一本是圣伯夫(Sainte-Beuve)的《伟大的法国作家》(Les Grands Ecrivains Fran?ais,Librairie Garnier Frères, 1926),共两册,第一册是拉马丁(Lamartine)和维尼(Vigny),第二册是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缪塞(Musset)和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这两册书主要介绍了这五位19世纪的法国诗人。这两本书的前衬右上角都有其法文签名“Founouen”。
一本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1844-1896)的《诗选》(Choix de poésies,Eugéne Fasquelle,1928)。法兰西学院弗朗索瓦·科佩(Fran?ois Coppée)做序。其前环衬的右上角有傅雷法文签名“Founouen”,左下角竖写有“傅怒安一九三一六月于巴黎”。全书大致按照主题(如忧伤、欢快、爱、幸福等)分为十一个部分。
傅雷在文学上自然也有着极高的鉴赏力,比如他对张爱玲作品曾有过精到的评论。从他的关于法国诗歌的藏书,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特别是对法国的诗歌其实是有着浓厚的兴趣的。只是从他后来的文字看,他并没有在诗歌鉴赏上有所发展。
四
以上这些只是笔者无意间所见的可以确定是傅雷藏书的书籍。还有一些书,也有可能是他的藏书,但是因为没有签名,无法确定。
比如,有一本保罗·兰多米(Paul Landormy)的《音乐史》(Histoire de la musique,Paul Mellottée,奇怪的是,这本书的出版时间并没有找到)。这本书以时间为序,从古代音乐一直讲到当时的音乐,年代和人物并举。扉页上引用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C’est le chant des siècles et la fleur de l’histoire; elle pousse sur la douleur comme sur la joie de l’humanité.”而这句话,正出自罗曼·罗兰的《古代音乐家》一书的导言。傅雷是这样翻译的:“它是世纪的歌声,历史的花朵;它在人类的痛苦与欢乐下面同样的滋长蓬勃。”(傅敏主编:《傅雷著译全书》第23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341页。)该书第12章就是海顿和莫扎特,第13章是贝多芬,第17章是肖邦,这些都是傅雷曾经关注过的音乐家,这些部分的内容都有看过的划痕。
还有一本勒内·福舒瓦(René Fauchois)的《贝多芬的爱情生活》(La vie d’amour de Beethoven,Ernest Flammarion,1928)。据作者自云,他试图写出贝多芬的“心的历史”,且这本书形式比较活泼,没有那些妨碍人阅读思路的注释、引文等(原书第七页)。为什么说这本书有可能是傅雷的呢?因为这本书和傅雷的《艺术哲学》(两册)以及《古代音乐家》一样,都有白色的硬壳封面,书脊上都用同样的字体写着书的作者和书名(下图)。
我们知道,傅雷对贝多芬、肖邦、莫扎特这些音乐家都十分关注,并曾作文介绍。比如他的《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肖邦的少年时代》《肖邦的壮年时代》和《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等,如果说这些关于音乐的书籍确是傅雷的藏书的话,也许他的这些文章的写作与这些书籍有着一定的关系。
类似这种情况的书籍恐怕还有。只是,现在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这几本书就是傅雷的藏书。笔者曾经拿这些书上的笔记请傅敏先生判断是否是其父亲的笔迹,他看到后,连连说“是他写的”。
从笔者所见的傅雷的藏书可以看到,傅雷当时所购买的书籍多是关于各种艺术门类的基础性的、入门性质的、相对通俗的书籍。这些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显得过时,有着不灭之价值。
更为珍贵的是,这中间有些书,不是一般的藏书,而是1930年前后年轻的傅雷在巴黎购买并翻阅,后来又进行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本。
这些书中保存了他的兴趣、他的眼光、他的气息,他青年时的负笈求学、壮年时的伏案翻译,都与这些书有关。略感遗憾的是,傅雷大概素爱整洁,这些书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划痕和批注。
五
这些图书从何而来?它们为什么会收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中?
笔者注意到这些书的后面多贴有一个邮票般大的“上海书店”的纸标签。上面写着价钱。比如罗丹口述,葛赛尔记录的《艺术论》定价100元,罗曼·罗兰的《古代音乐家》定价250元,博尔德的《艺术史二十讲》定价600元,这里的价钱都是手写体。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什么信息。
2021年12月2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孔海珠老师八十大寿,笔者上门祝寿。其间说到在图书馆看到的傅雷藏书。真是无巧不成书,孔老师当即说,那是她当年带着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道乾先生前去上海书店收购的傅雷的旧书。
孔海珠老师说她以前在上海书店工作,是1979年进文学所的。她说:
那时有空会回老单位找资料,旧书店的老员工会向我招手说近期收到什么好书的消息。傅雷家的书到旧书店后,他们也要找合适的单位买下来发挥作用。我让他们保留着,回去问王道乾先生,王道乾是副所长,他是法语专家,我跟他说傅雷家的书听说出售给旧书店了,有不少。我们所是不是买下来?他说他愿意去挑选一下。那天我带着所里不少人去的。
这真是意外的收获。
那么傅雷的藏书怎么又跑到上海书店呢?傅敏先生或许知道。2018年,值傅雷诞辰110周年纪念,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26卷《傅雷著译全书》。通过该书编辑,我和傅敏先生的夫人陈哲明老师取得联系。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告诉我他们就在上海,并邀请我到他们浦东的家中一聊。
2022年春节后的2月19日,我驱车前往他家。那天天气阴冷,但是屋里却温暖如春,85岁高龄的傅敏先生高瘦清峻,从楼梯缓缓而下。我将当时所看到确是傅雷藏书的封面和签名页打印出来,一一做了介绍,并带给他几份我所看到的几篇学界新发现的傅雷的佚文。
听了我的介绍后,关于傅雷先生的藏书的处理,傅敏先生缓慢而有力地说:
当时文革抄家,我爸爸自杀了之后,据说有人来偷他的东西,所以,就把整个东西都一起拉走,运到上海音乐学院去了。文革后期,音乐学院处理这件事,就把我爸爸的书都还给了我。可是我放哪呢?我就把这些书放在我爸爸的好朋友雷垣(按,雷垣系傅雷在大同学院同室寄宿的同窗好友)家里,雷垣家里有三层楼,我就把书放在他家里。其中,拉过去的时候我请罗新璋整理一下,因为罗新璋懂法文。我对他说,你需要的你就留下,他选了一部分他所需要的留下,其他的,他整理了一下。有一部分是我拉到了我舅舅朱人秀家里,这里头呢,罗新璋需要在那里整理,剩下的就给朱人秀处理了。主要的书呢,就放在雷垣家的三层楼那儿了,放在那儿大约有半年时间左右吧,后来呢,我也没办法,也不能老放在人家家里,后来就是我处理了,卖掉了。
关于傅敏先生所说的“有人来偷他的东西”,傅雷的好朋友刘海粟也说过这么一件事:
“一九七六年冬天,我的一个学生拿来一张画:《长城八达岭》,这是我解放初期送给怒安的。封门之后,小偷从屋顶爬进去偷出画来,卖到旧货店。我的学生从旧货店买了回来,真是叫人感慨万千!”(刘海粟:《傅雷二三事》,刘海粟著,沈虎编:《刘海粟散文》,花城出版社 1999年版,第244页。)
傅雷生前就收藏了一些名画,他去世后,这些东西便为小偷盯上了。
至此,傅雷藏书流传的经过,大致可以弄清楚了。
标签: